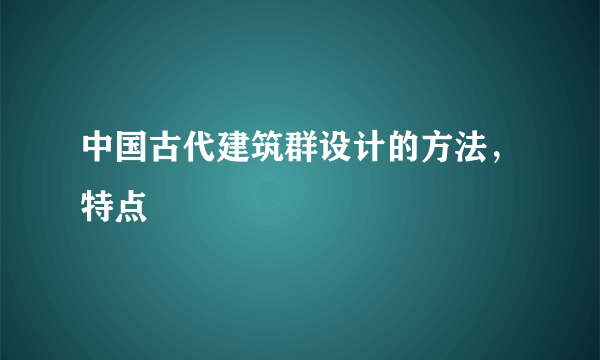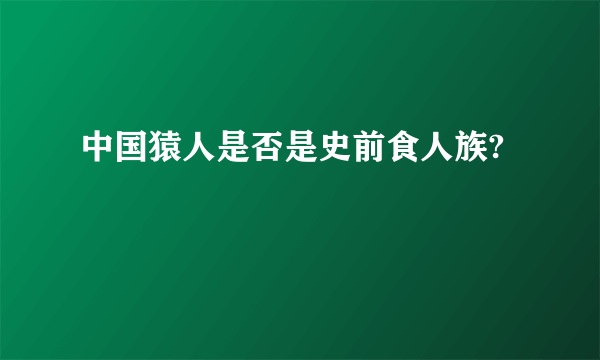中国人的思维方式
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:
自我超越有形有相的东西终归于毁灭,要实现真正的不朽,就要超越自我这个有限的存在。中国先哲将“道”作为超越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的永恒存在。但这个“道”又不是不可捉摸、高高在上的上帝,它“有情有信”,就在万事万物之中。理想人格的获得就在于与“道”自觉、自然而然地合和。道虽“有情有信”,它又超言绝象。要与“道”冥合,就需要超越一切形体和自己的生命。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中达到无限,在现实中实现永恒。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提升,不在躯壳上起念,追求某种精神境界,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在现实中的体现与应用。自我实现中国先哲的目的是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性,从中得到真正的精神享受,即所谓的“心中乐地”。这种实现完全是现世主义的,它主张在现世人生中实现最高理想,并不需要彼岸的永恒和幸福。因为永恒和幸福本来就在你的心中,随时可以实现和受用。中国人把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定为人生“三不朽”,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现世特征。然而,也同样由于这种现世的自我实现导致了中国人的功利主义、家族主义和个人主义。同追求永恒的精神境界正好形成明显的反差。这说明,任何事物都是把“双刃剑”。这种着眼于现世的自我实现既解释了中国人易于满足不思进取、长期安于小农生活的弊病,也成就了中华民族勤劳忍耐的美德。中庸之道中庸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,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:(1)执两用中,不走极端,如对圣人的描写,“宽而栗,严而温,柔而直,猛而仁”。(2)无过无不及,避免偏执,不偏激,追求平和。最明显体现在中医对身体阴阳二气的调节上。(3)得时勿失,时不我待,追求时中。至今仍有关于种小麦的农谚,“白露早,寒露迟,秋分种麦正当时”。(4)允执其中,保持平衡。(5)有原则地折衷。中庸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、医学、政治和人际关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它稳固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,缓和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,协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,至今对世界仍有重大意义。直觉思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思维,而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。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,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,相辅相成,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(整体思维、系统思维)的特征。它目的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表象特征,其基本形式常常通过“顿悟”来表现。道家的“悟道”、儒家的“豁然贯通”、佛教的“立地成佛”,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运用。就思维的精确性来看,直觉思维是一种模糊的思维方式。这是因为,自然界或宇宙的本质,不可能通过推理或分析来把握,只能通过直觉来领悟。中国人的许多概念、命题歧义丛生,正是这种思维造成的。所谓的“天人合一”,所谓的心通万物,都是这种思维的必然结果。整体思维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,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,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的特征。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主要有以下特点,(1)它形成了八卦、六十四卦、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,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。(2)宇宙整体和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具有统一的结构,遵从相同的演化法则,并由此导出天地一理、万物一马、宇宙全息的结论。整体思维对中国的历史、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。中国人素有的“大一统”思想,中医的“头痛医脚,脚痛医头”的整体疗法,以及中国文化偏重综合、弱于分析、概念的模糊性等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。意象思维意象思维方式亦称为象征,是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,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。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方式可分为三类:(1)符号意象思维,用某种符号来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则,如《易经》中的“---”“-”,各种道教、佛教的灵符。(2)玄想意象思维,用选择出的意象符号来象征事物本质或某种“形而上”的东西,如老子、庄子的“道”、玄学中的“无”“自然”,朱熹的“太极”“天理”等。(3)审美意象思维,通过塑造审美意象来达到某种带有文学艺术情趣的思想境界,如王维的诗、苏轼的词、中国的山水画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。中国传统意象思维的优点是富于灵感,带有跳跃性和创造性,但它的缺点是不够严密、精确,缺乏科学性。从这种思维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长于文学艺术的创造,而乏于科学技术的创新(很多人这样来解释这一问题;但是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,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,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,这一点大约也没有人可以否认。所以,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在此)。物极必反中国人普遍认为,事物的运动变化,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变。如《易经》:“无平不陂,无往不复”,《老子》:“正复为奇,善复为妖。”那么,事物在什么地步才发生这种转变呢?那就是,无论任何事物,到了盈满或顶点时,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。自汉代《淮南子》明确提出“物极必反”的命题后,它便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思维模式。这里的“极”,实际上是一种极限、顶点。之所以发生物极必反,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,当一方势力上升,达到顶点时,便转而消退;另一方则相反,由消而长,这时就发生物极必反。循环变易中国古人认为,“物极必反”只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一半路程。如果从事物的整个运动变化过程来说,则是一反一复、周而复始地循环运动的。老子一方面讲“道”生天地万物,同时又讲万物复归于“道”,整个宇宙都处在这个大循环之中。《易经》同样也倡导终则有始、反复其道的变化观。中国古人不但用这种循环往复的变化观解释万物,还用它来解释社会运动和朝代的兴替。邹衍的“五德终始”说,董仲舒的“三正三统”说,把中国的历史纳入一个永远的循环往复之中。以至于今天人们还常说“天下大势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”“皇帝轮流坐,今朝到我家”。万物一体中国先哲,无论儒家还是道家,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皆是“万物与我为一”。这个“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境界在儒家则表现为对万物的仁爱上,认为万物中的一草一木皆与我息息相关。在这种境界中,“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”。甚至认为虫鱼鸟兽皆有其存在的理由。在这里,已无主客之分,物我之别。人就是自然,自然就是人。自然界之所以“鸢飞鱼跃,一片生机,乃是因为在其中投射了人的仁爱胸怀,是主体体验的结果”。在道家则表现为“浑沌”,人与鸟兽同处,与万物并育,不知君子小人之分,亦不知牛马之别。一切皆按各自的本性发展,共同组成自然的整体。自然界之所以自由自在,一片生机,乃是人把自己那超越一切藩篱的精神体验投射到万物之中的结果。天人合一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,它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。它认为人与天不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,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、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。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儒家、佛教、道家三家思想都主张“天人合一”。在儒家看来,“天”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,人心中“天”赋“地”具有道德原则,这种“天人合一”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。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、欲望的蒙蔽,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。人类修行的目的,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,“求其放心”,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,这就是孔子所说的“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。在禅宗看来,人性本身就是佛性,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、欲望而不自觉,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、欲望都不是真实的,真如本性自然显现,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,因此,他们提出“烦恼即菩提,凡夫即佛”。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?从某种意义上说,仍有点像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。故禅宗语录有言:“悟得来,担柴挑水,皆是妙道。”“禅便如这老牛,渴来喝水,饥来吃草。”在道家看来,“天”是自然,“人”是自然的一部分。因此庄子说:“有人,天也;有天,亦天也。”天人本是合一的。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、道德规范,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,变得与自然不协调。人类修行的目的,便是“绝圣弃智”,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,将人性解放出来,重新复归于自然,达到一种“万物与我为一”的精神境界。穷理尽性中国古代哲人几乎都讲穷理和尽性,但他们所穷的“理”却是人心中天赋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;所尽的“性”是具有人类社会涵义的“性”或行为准则。其实“理”和“性”应该是合二而一的。“理”是从外在或天的角度说,而“性”是从内在或人的角度讲。二者的结合则通过“命”,故《中庸》有言:“天命之谓性。”其实,这里的“命”就是个体的人的生命——人生的具体经验(经历),而非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“命运”“命数”。其实,“理”在本质上就是“礼”,是社会政治、伦理原则的总称和一切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关系。这种原则本来是人类社会长时期形成的。但先古哲人将之上升为宇宙自然的总原则,再通过“天命”的手段,把它内在于万物中成为万物个体的“性”。穷理尽性就是认识这种“天然的秩序”,并切身践履,达到与自身化而为一的境界。因此,中国人讲穷理,虽然于《荀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公孙龙子》、《易经》等典籍中也表现出一些外向思维的倾向,体现出一些探求物理的特征,但由于先哲将人生的意义定位于“自身精神境界”的成就,因此,这些人的穷理最终仍然归于“尽性以至于命”。虽有惠施(与公孙龙子同为“名”家人物)对外物的探求,却被庄子批评为“迷于万物而不反”。由此可以看出,中国人科学思维薄弱的原因(关于这一问题,我仍然坚持逻辑思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,有些事物之间有因果的逻辑联系,但并非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关系,即有些事物有其因未必有其果。所以,完全根据了中国古人的这些特征或表现,就断定“中国古人科学思维薄弱”是没有说服力的)。情感体验中国人很注重情感体验层次上的意象思维,个人的情感需要、评价和态度在思维和处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使用。由于过分重视情感因素和心灵体验,导致中国人在思维上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,没有形成形式化和公理化的思维传统。在个人心灵体验中直接把握事物的意义,或从具体感受中抽象出一般原则,使中国人很自然地将主观情感投射到自然万物之中,使自然万物皆具有人的特点。它不但表现在哲学家认识外物的态度上,如曾点之乐,庄子的鱼之乐,还体现在文学家的创作主题上,如杜甫的“感时花溅泪”,关汉卿的“六月飞雪”,以及曹雪芹的“木石姻缘”。此外,中国人认为山川树木皆有灵气,封禅、祭河也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。明心见性这是禅宗的思维或成佛方式。自南北朝时竺道生首倡“一切众生皆有佛性”之说,佛性便被从神圣的彼岸拉回到每个人的心里。因此,慧能说“佛向心头做,莫向心外求”。所谓“明心见性”,就是明白自家的“本心”,见到自家的“本性”。这个心就是菩提心,这个“性”就是佛性。能否成佛,关键在于能否悟“本心”“本性”的真面目,悟到这个真面目,即使普通人也能成佛,悟不到这个道理,即使佛也变成了普通人。佛与凡夫本无差别,只在“迷”、“悟”之间。渐悟思维渐悟思维贯穿于中国古代各家思想之中。它的特点在于主体从思维的对象和内容方面作好必要的准备,经过某种契机的引发,突然认识到事物的全体和真相。认识到事物的真相或全体,在道家称为“悟道”;在儒家称为“豁然贯通”;在佛教称为“成佛。”在儒家,最明显地体现在程颐的“脱然贯通”和朱熹的“豁然贯通”说。他们认为,只有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,才能在“用力之久”的工夫中达到“豁然贯通”。故荀子对渐悟总结道:“思之思之,又重思之,思之不通,鬼神将通之,非鬼神之灵也,思之极也。”在佛教,渐悟又名“因缘见性”。认为人们只有通过积德修道的助缘,才能见性成佛。最著名的是神秀的渐悟偈:“身是菩提树,心如明镜台。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。”混沌思维混沌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,认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说、也无法说的。为此,儒、释、道三家皆将对世界的最终认识当作个人的直觉体验。这是一种“此中有真意,欲辩已忘言”的境界。为此,庄子曾举出了有趣的“浑沌凿窍”的故事。“南海的帝王叫倏,北海的帝王叫忽;中央之国的帝王叫浑沌,倏、忽经常到浑沌那里游玩,浑沌对他们很好。倏、忽想报答浑沌的友善。商量说:“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,用来呼息、吃饭,浑沌却没有,咱们给他凿个吧!”两人于是每天凿了一窍,凿了七天,七窍全俱,而浑沌却死了。混沌思维的结果就是认识到“万物一体”。这不但是一种认识的结果,还是人格提升的一种精神境界。无论儒、释、道观点上如何相异,但他们的最终境界都是一致的。如庄子的“天地一指也,万物一马也”,程颢的“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”,僧肇的“天地与我同根,万物与我一体”等等。躬身践履中国人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就高尚的人格,而高尚的人格不是通过知识积累所能达到的。因此,伴随成德的学问,自然形成一种切身践履圣人之言的思维。它具体表现在如何通过将圣人之教与自己的言行结合起来,最终成圣成贤。故《大学》在列了三纲领、八条目之后,直接道出“一是皆以身为本”。只有个体通过躬身实践,才能成为圣贤,受人尊敬。否则,便会被人斥为赵括马谡之流,不悟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的道理。当然,无论儒家、佛教和道家,所强调的躬身践履都与西方的科学实验是两回事。中国古人的躬身践履是对圣人之言的信仰和执行,在这里不存在怀疑,只存在印证。如果你印证不了,那说明你自身有问题,决不能在圣人之言上找毛病。其目的便是达到“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”的境界。格物致知中国宋明理学的认识方法,最早见于《大学》,是八条目中两条目。有理学派和心学派两种解释。理学派以程颐、朱熹的观点为代表,他们认为“格物”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,包括事物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;而“致知”则是利用类推的方法,将已得之理推广到万事万物之上。其具体方法在于读书讨论,应接事物和到具体事物中去发现。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,便会豁然贯通,达到万物之理为一的境界。心学派以陆九渊、王阳明的观点为代表。他们认为“心即理”,“格物”就是正心,认识本心,使心始终不离正道。至于外物如何,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。“致知”则是将内心中的道德原则即良知推广于万事万物之上,使万物皆具有吾心之良知。但是,无论程朱,还是陆王,最终都归于明了心中的本性,即道德本然,以达到儒家的“圣贤境界。”反求诸己中国人认为学问的目的不在于认识外物,而在于成就自身,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,因此,“反求诸己”,观察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最高人生价值的标准,便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一。孔子说: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孟子说:“反躬自问,正义不在我,纵是卑贱之人,我也不去恐吓他;反躬自问,正义在我,虽千军万马,我也不畏惧。”荀子也说:“君子每天要做三次反思,便可达到聪睿智达,行为无过。”那么,所谓的反思、反躬自问是思什么、问什么呢?简言之,就是反问自己的良心。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时,问问自己的良心,如果心安则为之,如果心不安而为之,则失去了反思的意义。反思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自身,成就自身的德行,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。通过自我反思,觉悟到道德原则乃我本然所有,自觉地依照道德原则而行,就叫“悟”。相反,不悟自己的本性,单纯追求知识的积累,则被批评为“迷于万物而不反”。顿悟思维禅宗六祖慧能提出的独特的悟道之方。它反对一切知识积累、只凭一介清明之心,单刀直入,直探至理真源,达到成佛的境界。但禅宗的顿悟亦不是完全无可捉摸的,它也有引导入悟的方法。一是疑念法,即通过提出问题,唤起疑念,久思不通,突然有得,求得觉悟。如:“问:如何是祖师西来意?曰:窗前柏树子。”二是暗示法,即通过暗示而不直接给出答案,启发人去尽心求解。如:禅宗中的“断指悟道。”三是遮掩法,即烘云托月,如慧能点悟神会(据《坛经·行由品第一》,我以为或应为“惠明”)时曾说:“不思善,不思恶,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。”言下神会恍然大悟。超佛越祖禅宗思维方式,它否定了彼岸的神圣偶像,靠自身的信念和觉悟,就能在现实生活中,在自己的心中,实现精神超越。这种境界既不脱离现实却又超越了现实,既不脱离自我却又超越了自我,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宗教的超越。正如禅宗语录所言,“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”。这种境界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和享受到。这种思维方式排除了彼岸与此岸的差别,取消了彼岸的偶像,在自己有限的存在中实现了无限和永恒。察己知人《吕氏春秋·察今》:“察己可以知人,察今可以知古。古今一也,人与我同也。”因此,人应该体认内在的自然本性,而不在于辨别外在的事物之理。因为吾性即人性,要认识外物和别人,只需认识自己就够了。所谓内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主要指共同的爱好、欲求以及理想。这些爱好、欲望和理想等,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解释。《吕氏春秋》认为人皆崇尚相同的秩序,有相似的欲望或理想;道家认为人皆有相似的崇尚自然的本性;儒家则以为人皆有相同的道德本心,皆喜欢合于理义的事情,皆希望实现“大同仁爱”的社会。所有这些相同或相似,一言以蔽之,皆因为各学派都认为人心中有一个“共识”,在这种共识下,可以推己及人、察己知人。已经流行于全世界的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(出自《论语》)的思想也源于此。辩证思维中国先哲善于从事物的有机联系、对立统一中认识和把握事物,具体表现在阴阳刚柔的对立、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对立统一、“和实生物”、“执两用中”的处事方法,以及“物极必反”的发展变化观。特别地,“执两用中”的处事法则形成了中国人宽厚仁和的民族特性;而“物极必反”的世界观则帮着中国人在困苦危难之中,始终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,使我们的民族从不消沉,永远处于活力和奋斗之中。安身乐命人生在世,有许多东西是超出个人的能力和欲求之外的。明知在人的能力之外而又要拼命追求,则不免陷入烦恼之中。故中国先哲从心灵上解除人的烦恼。孔子说:“尽人事,听天命。”孟子也说:“不知道它怎么来的,但它却来了的,都是命定的。”人在这些东西面前只有坦然处之,尽心尽力,至于那人力不能及处,只好任其自然了。庄子则提出,不但要承认天命,而且还要高高兴兴地接受它,顺应它,这样便能使心灵常常处在自由逍遥之中。所以他说:“通达生命的真实状况的,不去追求与生命无关之物;通达命运实情的,不去探讨人的理智无可奈何的东西。”这样才能安时处顺,无往而不乐。